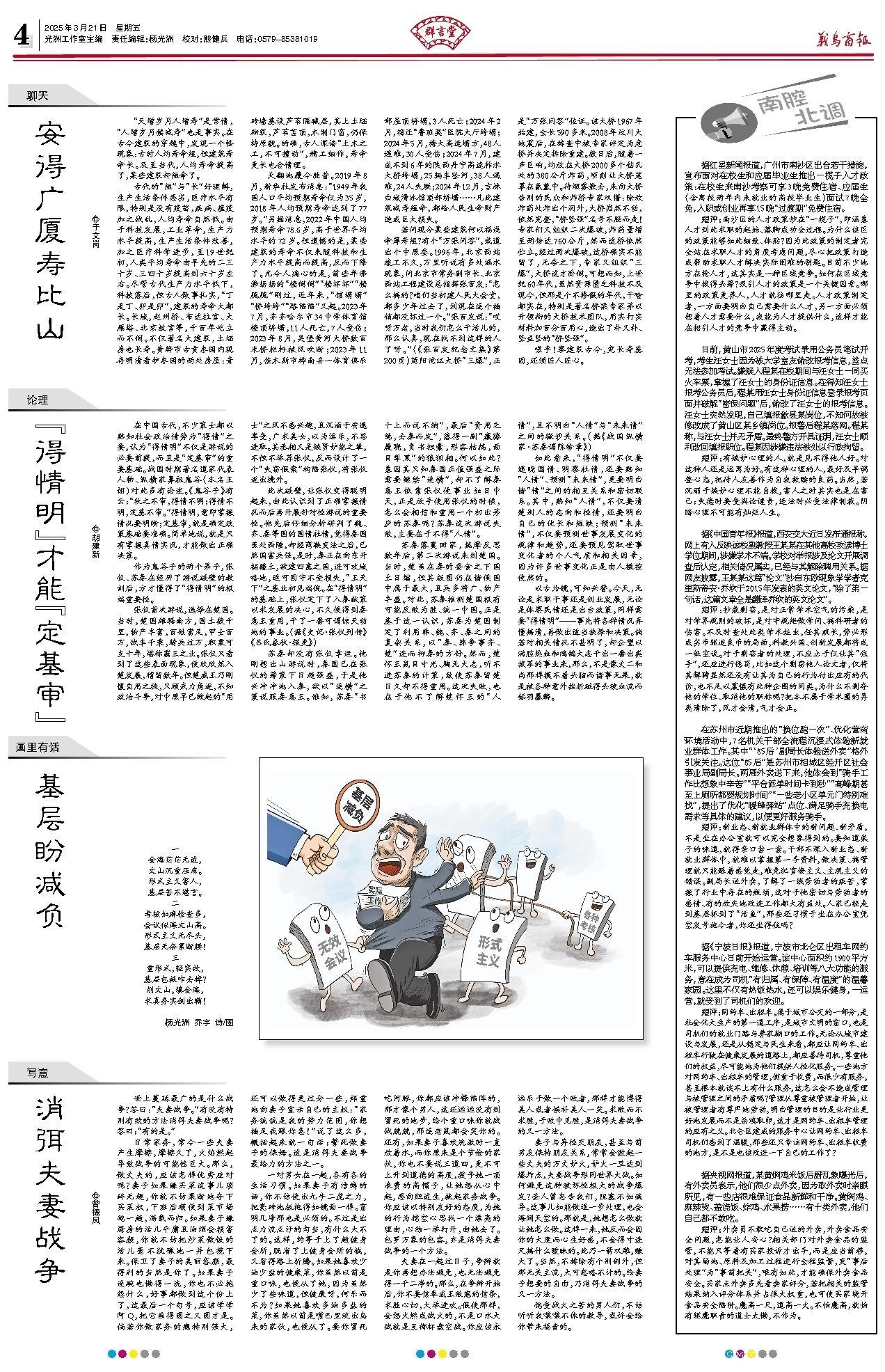在中国古代,不少策士都以熟知社会政治情势为“得情”之要,认为“得情明”不仅是游说的必要前提,而且是“定基审”的重要基础。战国时期著名道家代表人物、纵横家鼻祖鬼谷(本名王诩)对此多有论述。《鬼谷子》有云:“牧之不审,得情不明;得情不明,定基不审。”得情明,意即掌握情况要明晰;定基审,就是确定政策基础要准确。简单地说,就是只有掌握真情实况,才能做出正确决策。
作为鬼谷子的两个弟子,张仪、苏秦在经历了游说碰壁的教训后,方才懂得了“得情明”的极端重要性。
张仪首次游说,选择在楚国。当时,楚国雄踞南方,国土数千里,物产丰富,百姓富足,甲士百万,战车千乘,骑兵过万,积粟可支十年,堪称霸王之业。张仪只看到了这些表面现象,便欣欣然入楚发展,稽留数年。但楚威王乃刚愎自用之徒,只顾武力角逐,不知政治斗争,对中原早已掀起的“用士”之风不感兴趣,且沉湎于安逸享受,广求美女,以为淫乐,不思进取。其丞相又是嫉贤妒能之辈,不但不举荐张仪,反而设计了一个“失窃假案”构陷张仪,将张仪逐出境外。
此次碰壁,让张仪变得聪明起来,由此认识到了正确掌握情况而后再开展针对性游说的重要性。他先后仔细分析研判了魏、齐、秦等国的国情社情,觉得秦国虽处西陲,却经商鞅变法之后,已然国富兵强。是时,秦正在向东开拓疆土,欲建四塞之国,进可攻城略地,退可固守不受损失,“王天下”之基业初见端倪。在“得情明”的基础上,张仪定下了入秦献策以求发展的决心,不久便得到秦惠王重用,干了一番可谓惊天动地的事业。(据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《吕氏春秋·报更》)
苏秦却没有张仪幸运。他刚想出山游说时,秦国已在张仪的筹策下日趋强盛,于是他兴冲冲地入秦,欲以“连横”之策说服秦惠王。谁知,苏秦“书十上而说不纳”,最后“资用乏绝,去秦而发”,落得一副“羸滕履跷,负书担橐,形容枯槁,面目犁黑”的狼狈相。何以如此?盖因其只知秦国正值强盛之际需要继续“连横”,却不了解秦惠王依靠张仪使事业如日中天,正是放手使用张仪的时候,怎么会相信和重用一个初出茅庐的苏秦呢?苏秦这次游说失败,主要在于不得“人情”。
苏秦落寞回家,揣摩反思数年后,第二次游说来到楚国。当时,楚虽在秦的蚕食之下国土日缩,但其版图仍在诸侯国中属于最大,且兵多将广、物产丰盛。对此,苏秦推测楚国极有可能反败为胜、统一中国。正是基于这一认识,苏秦为楚国制定了利用韩、魏、齐、秦之间的复杂关系,以“秦、韩争事齐、楚”进而抑秦的方针。然而,楚怀王鼠目寸光、胸无大志,听不进苏秦的计策,致使苏秦留楚日久却不得重用。这次失败,也在于他不了解楚怀王的“人情”,且不明白“人情”与“未来情”之间的微妙关系。(据《战国纵横家·苏秦谓陈轸章》)
如此看来,“得情明”不仅要通晓国情、明察社情,还要熟知“人情”、预测“未来情”,更要明白诸“情”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密切联系。其中,熟知“人情”,不仅要清楚别人的志向和性情,还要明白自己的优长和短缺;预测“未来情”,不仅要预测世事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,还要预见驾驭世事变化者的个人气质和相关因素,因为许多世事变化正是由人操控使然的。
以古为镜,可知兴替。今天,无论是求职干事还是创业发展,无论是体察民情还是出台政策,同样需要“得情明”——事先将各种情况弄懂搞清,再做出适当抉择和决策。倘若对相关情况不甚明了,却企望以满腔热血和鸿鹄大志干出一番出类拔萃的事业来,那么,不是像丈二和尚那样摸不着头脑而诸事无果,就是被各种意外挫折碰得头破血流而铩羽暴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