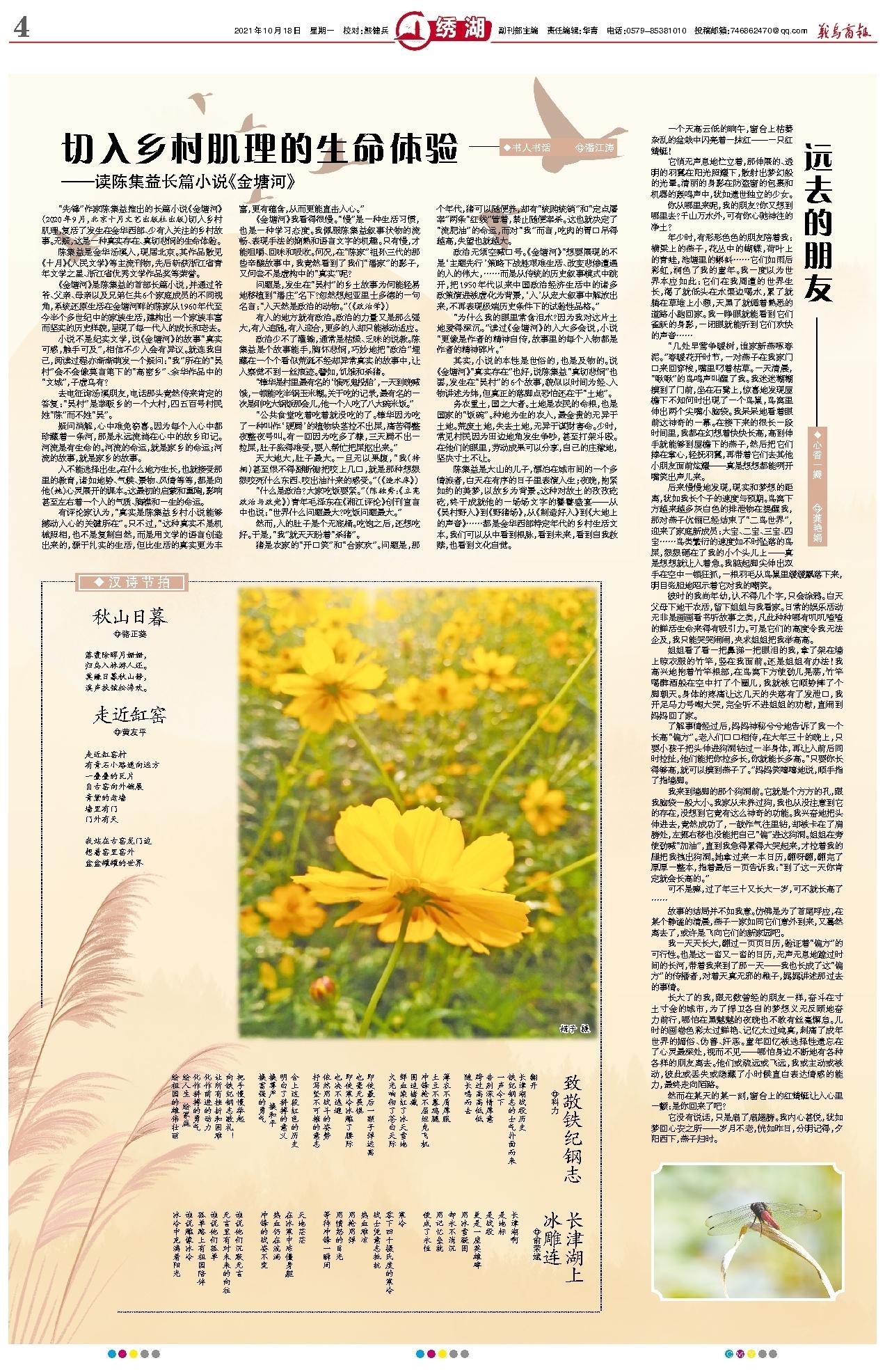一个天高云低的晌午,窗台上枯萎杂乱的盆栽中闪亮着一抹红——一只红蜻蜓!
它悄无声息地伫立着,那伸展的、透明的羽翼在阳光照耀下,散射出梦幻般的光晕。清丽的身影在防盗窗的包裹和机器的轰鸣声中,犹如遗世独立的少女。
你从哪里来呢,我的朋友?你又想到哪里去?千山万水外,可有你心驰神往的净土?
年少时,有形形色色的朋友陪着我:横梁上的燕子,花丛中的蝴蝶,荷叶上的青蛙,池塘里的蝌蚪……它们如雨后彩虹,润色了我的童年。我一度以为世界本应如此:它们在我周遭的世界生长,渴了就低头在水渠边喝水,累了就躺在草堆上小憩,天黑了就循着熟悉的道路小跑回家。我一睁眼就能看到它们雀跃的身影,一闭眼就能听到它们欢快的声音……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春暖花开时节,一对燕子在我家门口来回穿梭,嘴里叼着枯草。一天清晨,“啾啾”的鸟鸣声叫醒了我。我迷迷糊糊摸到了门前,坐在石凳上,惊喜地发现屋檐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鸟巢,鸟窝里伸出两个尖嘴小脑袋。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神奇的一幕。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在幻想着快快长高,高到伸手就能够到屋檐下的燕子,然后把它们捧在掌心,轻抚羽翼,再带着它们去其他小朋友面前炫耀——真是想想都能咧开嘴笑出声儿来。
后来慢慢地发现,现实和梦想的距离,犹如我长个子的速度与预期。鸟窝下方越来越多灰白色的排泄物在提醒我,那对燕子伉俪已经结束了“二鸟世界”,迎来了家庭新成员: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、四宝……鸟类繁衍的速度如不时坠落的鸟屎,狠狠砸在了我的小个头儿上——真是想想就让人着急。我踮起脚尖伸出双手在空中一顿狂抓,一根羽毛从鸟巢里缓缓飘落下来,明目张胆地昭示着它对我的嘲笑。
彼时的我尚年幼,认不得几个字,只会涂鸦。白天父母下地干农活,留下姐姐与我看家。日常的娱乐活动无非是画画看书听故事之类,凡此种种哪有叽叽喳喳的鲜活生命来得有吸引力。可是它们的高度令我无法企及,我只能哭哭闹闹,央求姐姐把我举高高。
姐姐看了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我,拿了架在墙上晾衣服的竹竿,竖在我面前。还是姐姐有办法!我高兴地抱着竹竿根部,在鸟窝下方使劲儿晃荡,竹竿喝醉酒般在空中打了个圈儿,我就被它顺势摔了个脚朝天。身体的疼痛让这几天的失落有了发泄口,我开足马力号啕大哭,完全听不进姐姐的劝慰,直闹到妈妈回了家。
了解事情经过后,妈妈神秘兮兮地告诉了我一个长高“偏方”。老人们口口相传,在大年三十的晚上,只要小孩子把头伸进狗洞钻过一半身体,再让人前后同时拉扯,他们能把你拉多长,你就能长多高。“只要你长得够高,就可以摸到燕子了。”妈妈笑嘻嘻地说,顺手指了指墙脚。
我来到墙脚的那个狗洞前。它就是个方方的孔,跟我脑袋一般大小。我家从未养过狗,我也从没注意到它的存在,没想到它竟有这么神奇的功能。我兴奋地把头伸进去,竟然成功了,一鼓作气往里钻,却被卡在了肩膀处,左挪右移也没能把自己“偏”进这狗洞。姐姐在旁使劲喊“加油”,直到我急得累得大哭起来,才拉着我的腿把我拽出狗洞。她拿过来一本日历,翻呀翻,翻完了厚厚一整本,指着最后一页告诉我:“到了这一天你肯定就会长高的。”
可不是嘛,过了年三十又长大一岁,可不就长高了……
故事的结局并不如我意。仿佛是为了首尾呼应,在某个静谧的清晨,燕子一家如同它们意外到来,又蓦然离去了,或许是飞向它们的新家园吧。
我一天天长大,翻过一页页日历,验证着“偏方”的可行性。也是这一沓又一沓的日历,无声无息地蹚过时间的长河,带着我来到了那一天——我也长成了这“偏方”的传播者,对着天真无邪的稚子,娓娓讲述那过去的事情。
长大了的我,跟无数曾经的朋友一样,奋斗在寸土寸金的城市,为了捍卫各自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奋力前行,哪怕在黑魆魆的夜晚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儿时的画卷色彩太过鲜艳、记忆太过纯真,刺痛了成年世界的媚俗、伪善、奸恶。童年回忆被选择性遗忘在了心灵最深处,视而不见——哪怕身边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离去。他们或疏远或飞远,我或主动或被动,彼此或丢失或隐藏了小时候直白表达情感的能力,最终走向陌路。
然而在某天的某一刻,窗台上的红蜻蜓让人心里一颤:是你回来了吧?
它没有说话,只是扇了扇翅膀。我内心甚悦,犹如梦回心安之所——岁月不老,恍如昨日,分明记得,夕阳西下,燕子归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