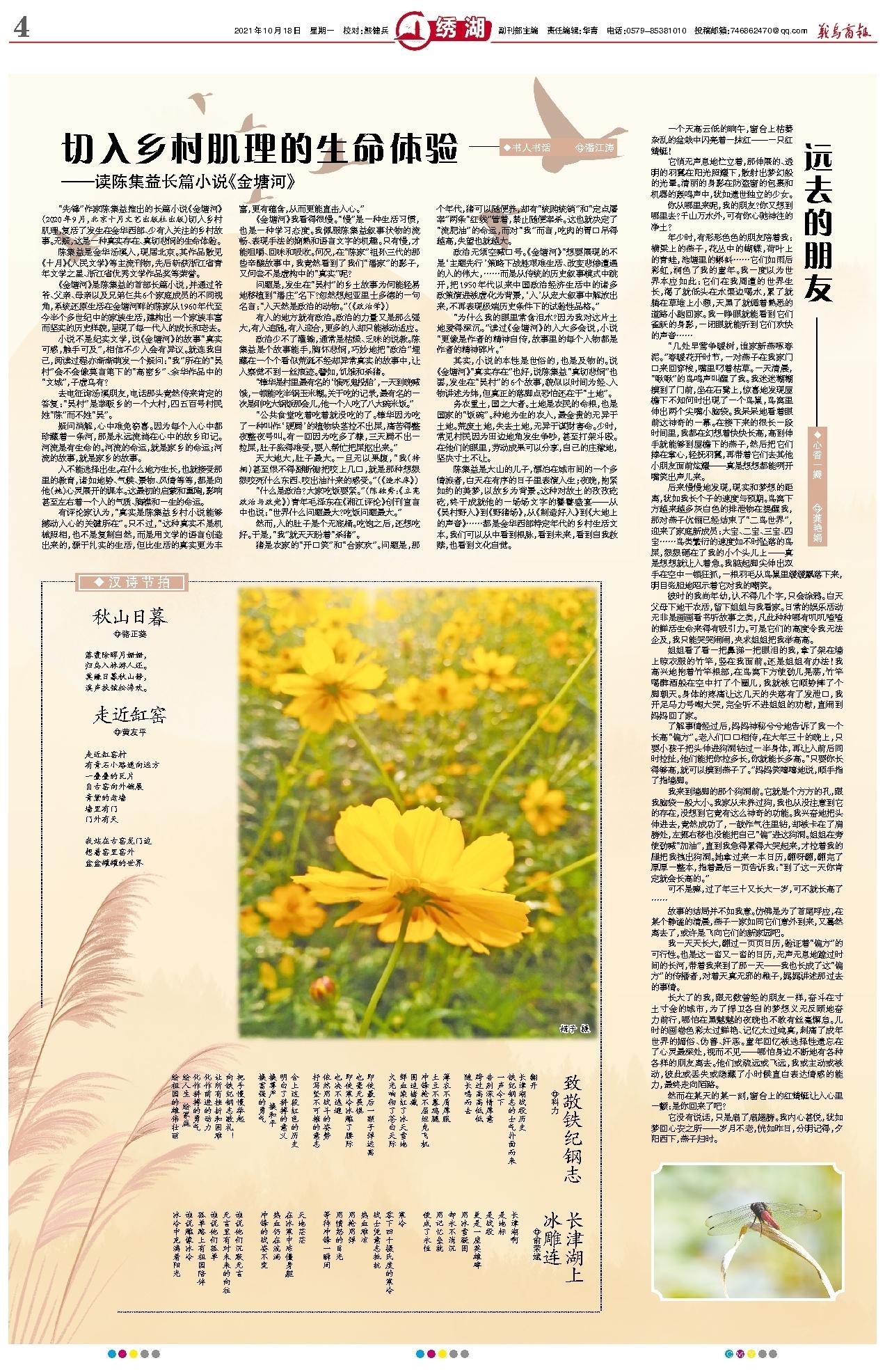潘江涛
“先锋”作家陈集益推出的长篇小说《金塘河》(2020年9月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)切入乡村肌理,复活了发生在金华西部、少有人关注的乡村故事。无疑,这是一种真实存在、真切悲悯的生命体验。
陈集益是金华汤溪人,现居北京。其作品散见《十月》《人民文学》等主流刊物,先后斩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、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荣誉。
《金塘河》是陈集益的首部长篇小说,并通过爷爷、父亲、母亲以及兄弟仨共6个家庭成员的不同视角,系统还原生活在金塘河畔的陈家从196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中的家族生活,建构出一个家族丰富而坚实的历史样貌,呈现了每一代人的成长和老去。
小说不是纪实文学,说《金塘河》的故事“真实可感,触手可及”,相信不少人会有异议。就连我自己,阅读过程亦渐渐萌发一个疑问:“我”所在的“吴村”会不会像莫言笔下的“高密乡”、余华作品中的“文城”,子虚乌有?
去电征询汤溪朋友,电话那头竟然传来肯定的答复:“吴村”是莘畈乡的一个大村,四五百号村民姓“陈”而不姓“吴”。
疑问消解,心中难免窃喜。因为每个人心中都珍藏着一条河,那是永远流淌在心中的故乡印记。河流是有生命的。河流的命运,就是家乡的命运;河流的故事,就是家乡的故事。
人不能选择出生。在什么地方生长,也就接受那里的教育,诸如地势、气候、景物、风情等等,都是向他(她)心灵展开的课本。这最初的启蒙和熏陶,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个人的气质、胸襟和一生的命运。
有评论家认为,“真实是陈集益乡村小说能够撼动人心的关键所在”。只不过,“这种真实不是机械照相,也不是复制自然,而是用文学的语言创造出来的,源于扎实的生活,但比生活的真实更为丰富,更有蕴含,从而更能直击人心。”
《金塘河》我看得很慢。“慢”是一种生活习惯,也是一种学习态度。我佩服陈集益叙事状物的流畅、表现手法的娴熟和语言文字的机趣。只有慢,才能咀嚼、回味和吸收。何况,在“陈家”祖孙三代的那些辛酸故事中,我竟然看到了我们“潘家”的影子,又何尝不是虚构中的“真实”呢?
问题是,发生在“吴村”的乡土故事为何能轻易地移植到“潘庄”名下?忽然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:“人天然是政治的动物。”(《政治学》)
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。政治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,有人追随,有人迎合,更多的人却只能被动适应。
政治少不了灌输,通常是枯燥、乏味的说教。陈集益是个故事能手,胸怀悲悯,巧妙地把“政治”埋藏在一个个看似荒诞不经却异常真实的故事中,让人察觉不到一丝痕迹。譬如,饥饿和杀猪。
“樟华是村里最有名的‘饿死鬼投胎’,一天到晚喊饿,一顿能吃半锅玉米糊。关于吃的记录,最有名的一次是刚吃大锅饭那会儿,他一个人吃了八大碗米饭。”
“公共食堂吃着吃着就没吃的了。樟华因为吃了一种叫作‘硬屙’的植物块茎拉不出屎,痛苦得整夜整夜号叫。有一回因为吃多了糠,三天屙不出一粒屎,肚子胀得难受,要人帮忙把屎抠出来。”
天大地大,肚子最大。一旦无以果腹,“我(梓桐)甚至恨不得掰断锄把咬上几口,就是那种想狠狠咬死什么东西、咬出油汁来的感受。”(《造水库》)
“什么是政治?大家吃饭要紧。”(陈独秀:《立宪政治与政党》)青年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宣言中也说: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?吃饭问题最大。”
然而,人的肚子是个无底桶。吃饱之后,还想吃好。于是,“我”就天天盼着“杀猪”。
猪是农家的“开口笑”和“合家欢”。问题是,那个年代,猪可以随便养,却有“统购统销”和“定点屠宰”两条“红线”管着,禁止随便宰杀。这也就决定了“流肥油”的命运,而对“我”而言,吃肉的胃口吊得越高,失望也就越大。
政治无须空喊口号。《金塘河》“想要展现的不是‘主题先行’策略下战胜艰难生活、改变悲惨遭遇的人的伟大,……而是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中跳开,把19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政策演进被虚化为背景,‘人’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,不再表现极端历史条件下的试验性品格。”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读过《金塘河》的人大多会说,小说“更像是作者的精神自传,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的精神碎片。”
其实,小说的本性是世俗的,也是及物的。说《金塘河》“真实存在”也好,说陈集益“真切悲悯”也罢,发生在“吴村”的6个故事,貌似以时间为经、人物讲述为纬,但真正的落脚点恐怕还在于“土地”。
务农重土,国之大者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,也是国家的“饭碗”。种地为生的农人,最金贵的无异于土地。荒废土地,失去土地,无异于谋财害命。少时,常见村民因为田边地角发生争吵,甚至打架斗殴。在他们的眼里,劳动成果可以分享,自己的庄稼地,坚决寸土不让。
陈集益是大山的儿子,漂泊在城市间的一个多情旅者,白天在有序的日子里表演人生;夜晚,抱紧如约的美梦,以故乡为背景。这种对故土的孜孜矻矻,终于成就他的一场场文字的饕餮盛宴——从《吴村野人》到《野猪场》,从《制造好人》到《大地上的声音》……都是金华西部特定年代的乡村生活文本,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根脉,看到未来,看到自我救赎,也看到文化自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