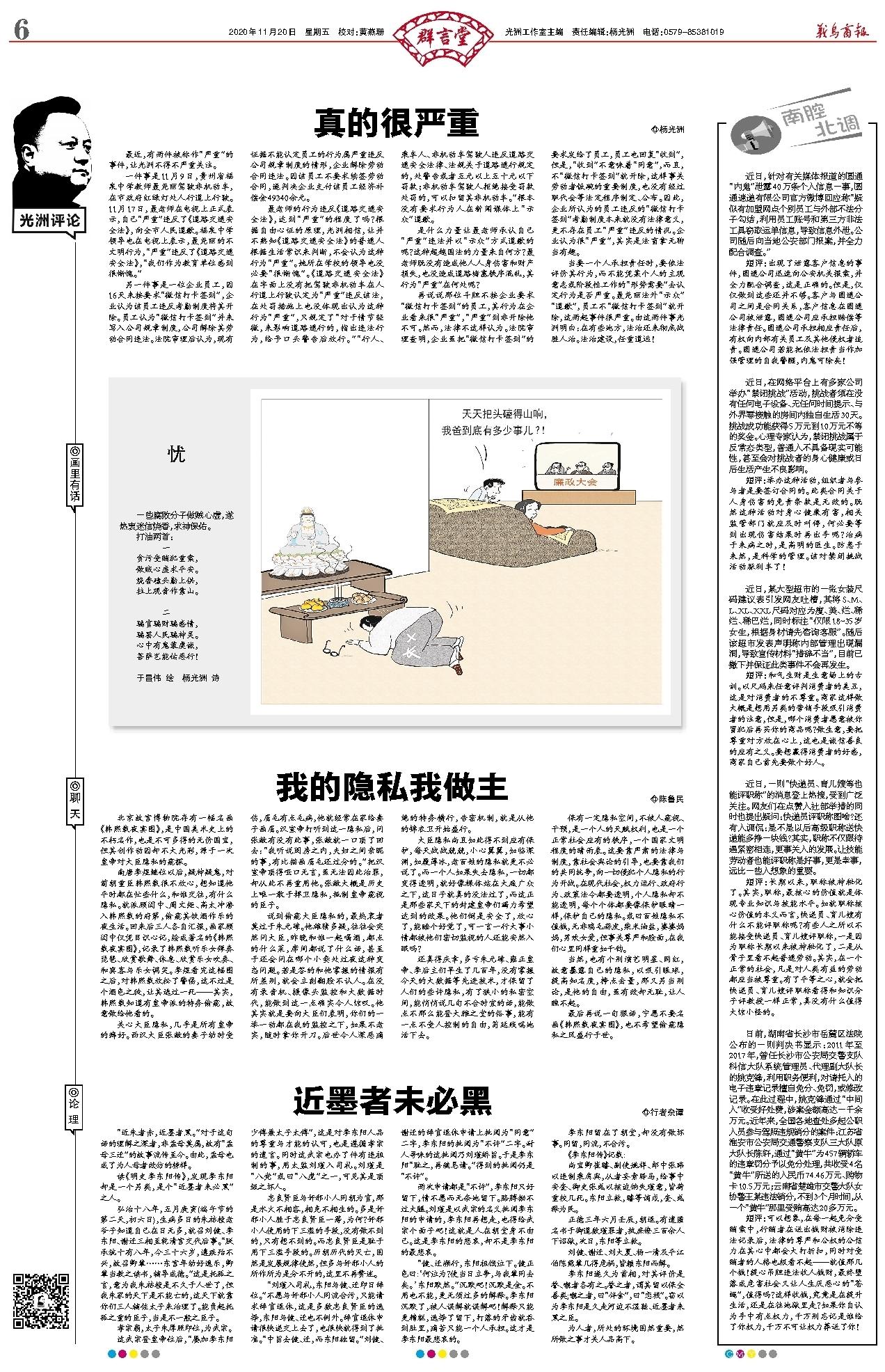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”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之深者,非孟母莫属,故有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流传至今。由此,孟母也成了为人母者效仿的榜样。
读《明史李东阳传》,发现李东阳却是一个另类,是个“近墨者未必黑”之人。
弘治十八年,五月庚寅(端午节的第二天,初六日),生病多日的朱祐樘老爷子知道自己在日无多,就召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三相至乾清宫交代后事。“朕承统十有八年,今三十六岁,遘疾殆不兴,故召卿辈……东宫年幼好逸乐,卿辈当教之读书,辅导成德。”这是托孤之言,意为我朱祐樘是不久于人世了,但我朱家的天下是不能亡的,这天下就靠你们三人辅佐太子来治理了。能负起托孤之重的臣子,当是不一般之臣子。
孝宗崩,太子朱厚照即位,为武宗。
这武宗登皇帝位后,“屡加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”,这是对李东阳人品的尊重与才能的认可,也是遵循孝宗的遗言。同时这武宗也办了件有违祖制的事,用太监刘瑾入司礼。刘瑾是“八党”或曰“八虎”之一,可见其是顶级之坏人。
忠良贤臣与奸邪小人同朝为官,那是水火不相容,相克不相生的。多是奸邪小人胜于忠良贤臣一筹,为何?奸邪小人使用的下三滥的手段,没有做不到的,只有想不到的。而忠良贤臣是耻于用下三滥手段的。历朝历代的灭亡,固然是发展规律使然,但多与奸邪小人的所作所为是分不开的,这里不再赘述。
“刘瑾入司礼,东阳与健、迁即日辞位。”不愿与奸邪小人同流合污,只能请求辞官退休,这是多数忠良贤臣的选择,东阳与健、迁也不例外。辞官退休申请很快递交上去了,也很快就得到了批准。“中旨去健、迁,而东阳独留。”刘健、谢迁的辞官退休申请上批阅为“同意”二字,李东阳的批阅为“不许”二字。耐人寻味的这批阅乃刘瑾矫旨。于是李东阳“耻之,再疏恳请。”得到的批阅仍是“不许”。
两次申请都是“不许”,李东阳只好留下,情不愿而无奈地留下。胳膊拗不过大腿。刘瑾是以武宗的名义批阅李东阳的申请的,李东阳再想走,也得给武宗个面子吧!这就是人在朝堂身不由己。这是李东阳的悲哀,却不是李东阳的最悲哀。
“健、迁濒行,东阳祖饯泣下。健正色曰:‘何泣为?使当日立争,与我辈同去矣。’东阳默然。”沉默吧!沉默是金。不用也不能,更无须过多的解释。李东阳沉默了,被人误解就误解吧!解释只能更糟糕,选择了留下,打落的牙齿就吞到肚里,痛苦只能一个人承担。这才是李东阳最悲哀的。
李东阳留在了朝堂,却没有做坏事。同留,同流,不合污。
《李东阳传》记载:
尚宝卿崔璿、副使姚祥、郎中张玮以违制乘肩舆,从者妄索驿马,给事中安奎、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,皆荷重校几死。东阳立救,璿等谪戍,奎、彧释为民。
正德三年六月壬辰,朝退。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,执庶僚三百余人下诏狱,次日,东阳等立救。
刘健、谢迁、刘大夏、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,皆赖东阳而解。
李东阳遂久为首相,对其评价是誉、嘲者各有之。誉之者,谓其留以保全善类;嘲之者,曰“伴食”,曰“恋栈”。窃以为李东阳是久走河边不湿鞋、近墨者未黑之臣。
为人者,所处的环境固然重要,然所做之事才关人品高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