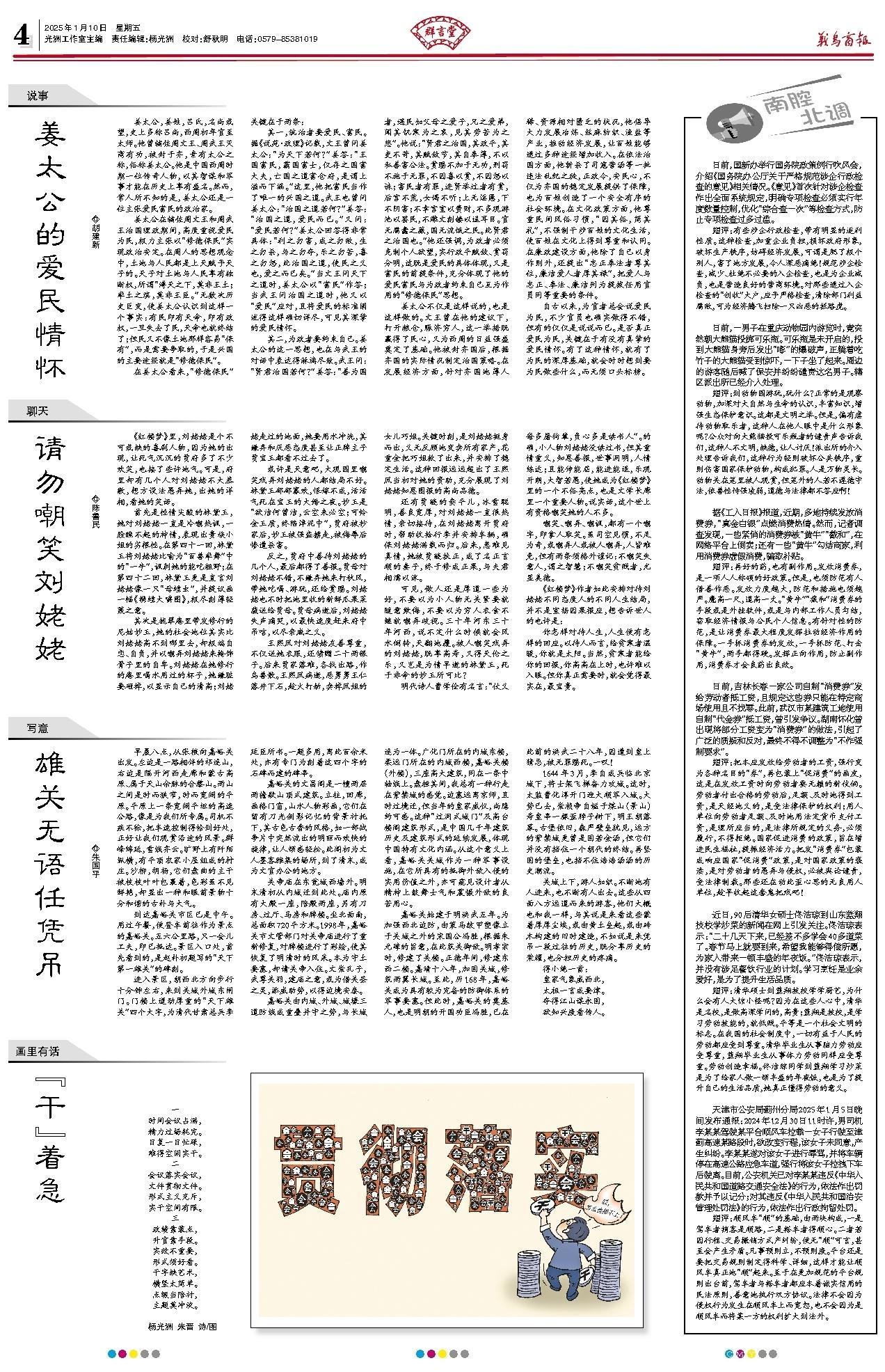早晨八点,从张掖向嘉峪关出发。左边是一路相伴的祁连山,右边是隔开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、属于天山余脉的合黎山。两山之间是时而狭窄,时而宽阔的平原。平原上一条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,像是为我们所专属。司机不疾不徐,把车速控制得恰到好处,正好让我们观赏沿途的风景。群峰绵延,雪线齐云。旷野上有阡陌纵横,有平顶农家小屋组成的村庄。沙柳,胡杨,它们盘曲的主干被枝枝叶叶包裹着,色彩虽不见鲜艳,却显出一种和眼前景物十分和谐的古朴与大气。
到达嘉峪关市区已是中午。用过午餐,便登车前往作为景点的嘉峪关。五六公里路,只一会儿工夫,即已抵达。景区入口处,首先看到的,是赵朴初题写的“天下第一雄关”的碑刻。
进入景区,朝西北方向步行十分钟左右,来到关城外城东闸门。门楼上遒劲厚重的“天下雄关”四个大字,为清代甘肃总兵李廷臣所书。一题多用,离此百余米处,亦有专门为刻着这四个字的石碑而建的碑亭。
嘉峪关的文昌阁是一幢两层两檐歇山顶式建筑。立柱,回廊,画格门窗,山水人物彩画,它们在留有刀光剑影记忆的背景衬托下,其古色古香的风格,如一部战争片中突然流出的明丽而欢快的旋律,让人顿感轻松。此阁初为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,到了清末,成为文官办公的地方。
关帝庙在东瓮城西墙外。明末清初从内城迁到此处。庙内原有大殿一座,陪殿两座,另有刀房、过厅、马房和牌楼。坐北面南,总面积720平方米。1998年,嘉峪关市文管部门对关帝庙进行了重新修复,对牌楼进行了彩绘,使其恢复了明清时的风采。本为守土要塞,却请关帝入住。文崇孔子,武尊关羽,建庙之意,或为借关圣之灵,添威助势,以得边境安泰。
嘉峪关由内城、外城、城壕三道防线成重叠并守之势,与长城连为一体。广化门所在的内城东楼,柔远门所在的内城西楼,嘉峪关楼(外楼),三座高大建筑,同在一条中轴线上。盘桓其间,我总有一种行走在紫禁城的感觉。边塞远离京师,且时过境迁,但当年的皇家威仪,尚隐约可感。这种“过洞式城门”及高台楼阁建筑形式,是中国几千年建筑历史及建筑形式的延续发展,体现中国特有文化内涵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嘉峪关关城作为一种军事设施,在它所具有的抵御外敌入侵的实用价值之外,亦可窥见设计者从精神上鼓舞士气和震慑外敌的良苦用心。
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。为加强西北边防,由策马披甲塑像立于关城之外的宋国公冯胜,根据朱元璋的旨意,在此筑关御敌。明孝宗时,修建了关楼。正德年间,修建东西二楼。嘉靖十八年,加固关城,修筑两翼长城。至此,历168年,嘉峪关成为具有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的军事要塞。但此时,嘉峪关的奠基人,也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冯胜,已在此前的洪武二十八年,因遭到皇上猜忌,被无罪赐死。一叹!
1644年3月,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,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。这时,太监曹化淳开门迎大顺军入城。大势已去,崇祯帝自缢于煤山(景山)寿皇亭一棵歪脖子树下,明王朝落幕。古堡依旧,森严壁垒犹见,远方的紫禁城更曾是固若金汤,但它们并没有挡住一个朝代的终结。再坚固的堡垒,也挡不住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。
关城上下,游人如织。不断地有人进来,也不断有人出去。这些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客,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,与其说是来看这些蒙着厚厚尘埃,或由黄土垒起,或由砖木构建的旧时建造,不如说是来凭吊一段过往的历史,既分享历史的荣耀,也分担历史的疼痛。
得小绝一首:
皇家气象威西北,
太祖一言成要津。
夺得江山谋永固,
欲知兴废看传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