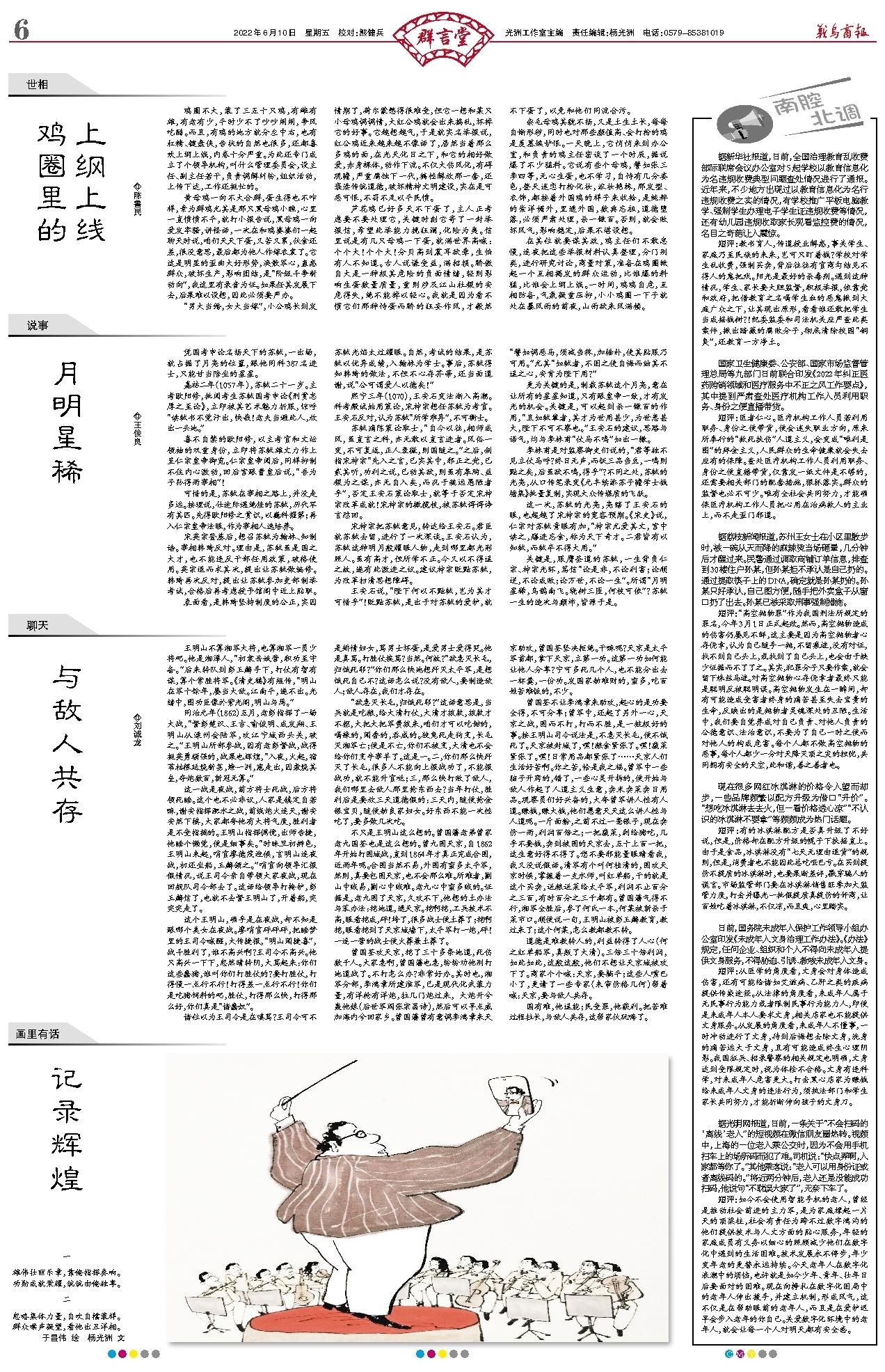凭国考申论名扬天下的苏轼,一出场,就占据了月亮的位置,跟他同科387名进士,只能甘当陪坐的星星。
嘉祐二年(1057年),苏轼二十一岁。主考欧阳修,批阅考生苏轼国考申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立即被其艺术魅力折服,惊呼“读轼书不觉汗出,快哉!老夫当避此人,放出一头地。”
喜不自禁的欧阳修,以主考官和文坛领袖的双重身份,立即将苏轼雄文力作上呈仁宗皇帝御览。仁宗皇帝阅后,同样抑制不住内心激动,回后宫跟曹皇后说,“吾为子孙得两宰相”!
可惜的是,苏轼在宰相之路上,并没走多远。按理说,仕途际遇绝佳的苏轼,历代罕有其匹。先得欧阳修之赏识,以巍科擢第;再入仁宗皇帝法眼,作为宰相人选培养。
宋英宗登基后,想召苏轼为翰林、知制诰。宰相韩琦反对。理由是,苏轼虽是国之大才,也不能违反干部任用政策,破格使用。英宗退而求其次,提出让苏轼做编修。韩琦再次反对,提出让苏轼参加吏部制举考试,合格后再考虑授予馆阁中近上贴职。
表面看,是韩琦坚持制度的公正,实因苏轼光焰太过耀眼。自然,考试的结果,是苏轼以优异成绩,入翰林为学士。事后,苏轼得知韩琦的做法,不但不心存芥蒂,还当面道谢,说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!”
熙宁三年(1070),王安石变法渐入高潮。科考殿试始用策论,宋神宗想任苏轼为考官。王安石反对,认为苏轼“所学乖异”,不可衡士。
苏轼痛陈策论取士,“自今以往,相师成风,虽直言之科,亦无敢以直言进者。风俗一变,不可复返,正人衰微,则国随之。”之后,剑指宋神宗“先入之言,已实其中,邪正之党,已贰其听,功利之说,已动其欲,则虽有皋陶、益稷为之谋,亦无自入矣,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”,否定王安石策论取士,就等于否定宋神宗改革成就!宋神宗的橄榄枝,被苏轼谔谔诤言怼回。
宋神宗把苏轼意见,转达给王安石。君臣就苏轼去留,进行了一次深谈。王安石认为,苏轼这种明月般耀眼人物,走到哪里都光彩照人。虽有高才,但所学不正。今又以不得逞之故,遂有此激进之议。建议神宗贬黜苏轼,为改革扫清思想障碍。
王安石说,“陛下何以不黜轼,岂为其才可惜乎”!贬黜苏轼,是出于对苏轼的爱护,就“譬如调恶马,须减刍秣,加棰朴,使其贴服乃可用。”尤其“如轼者,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,安肯为陛下用?”
更为关键的是,制裁苏轼这个月亮,意在让所有的星星知道,只有跟皇帝一致,才有发光的机会。关键是,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,“且如轼辈者,其才为世用甚少,为世患甚大,陛下不可不察也。”王安石的建议,思路与语气,均与李林甫“仗马不鸣”如出一辙。
李林甫是对监察御史们说的,“君等独不见立仗马呼?终日无声,而饫三品刍豆,一鸣则黜之矣,后虽欲不鸣,得乎”?不同之处,苏轼的光亮,从口传笔录变《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》批量复制,实现大众传媒质的飞跃。
这一次,苏轼的光亮,亮瞎了王安石的眼,也超越了宋神宗的宽容预期。《宋史》说,仁宗对苏轼青眼有加,“神宗尤爱其文,宫中读之,膳进忘食,称为天下奇才。二君皆有以知轼,而轼卒不得大用。”
关键是,服膺圣道的苏轼,一生背负仁宗、神宗光环,笃信“论是非,不论利害;论顺逆,不论成败;论万世,不论一生”。所谓“月明星稀,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,何枝可依”?苏轼一生的造次与颠沛,皆源于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