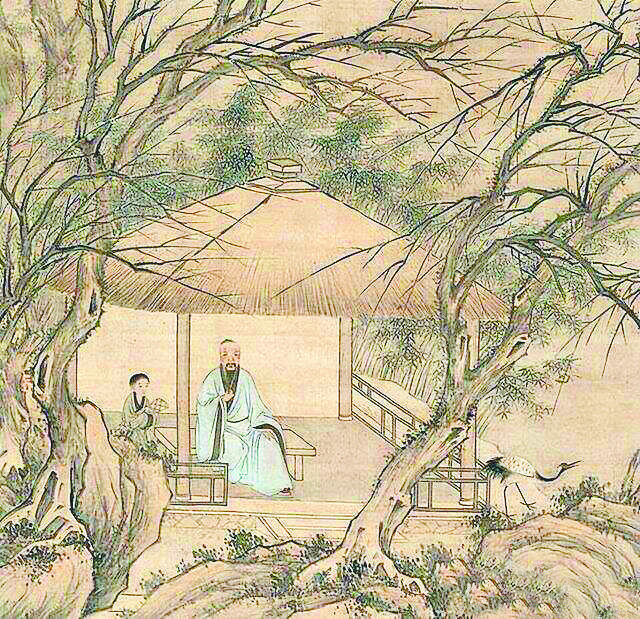绣湖之于义乌,犹如西湖之于杭州,在义乌人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宋、元时期,绣湖即为观景游赏之地,有众多文人墨客为之吟咏,并留下了许多诗篇佳作,他们各自用诗的语言道尽人生物语,说尽悲欢离合,即使时光荏苒,相隔千年,依然感动你我,触动心底事。
南宋淳熙六年(1179年),爱国诗人陆游在入闽赴任途中路过绣湖,赋有《题绣川驿》诗一首。其诗云:“绣川池阁记曾游,落日栏边特地愁。白首即今行万里,淡烟依旧送孤舟。归心久负鲈鱼鲙,春色初回杜若洲。会买一蓑来钓雨,凭谁先为谢沙鸥。”
陆游所写诗中的“绣川”,即今之绣湖,又名绣川湖。“绣川驿”是置于其中的一个驿站。“杜若”,为一种多年生的香草;“杜若洲”,即言丛生杜若的水洲,也是古绣湖中的一景。屈原《九歌·湘君》:“采芳洲兮杜若,将以遗兮下女。”明代王袆在《春日绣湖上与德元同行》一诗中,则写有“漠漠芙蓉浦,依依杜若洲”之句。“沙鸥”,是栖息在沙滩或沙洲上的一种鸥鸟。因为沙鸥是一种个体生活的鸟类,常常独自栖息在无人的沙洲上,故在诗词中常常被用来象征那些不知归宿的漂泊者;但沙鸥又有些傲岸,它常自由地翱翔于水上,漫天飞翔,所以有时也用来表示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。
在此诗中,陆游深情地回忆起了曾经游览过的绣川池阁。在落日的余晖中,诗人独自站在驿站的栏杆边极目远眺,感受着岁月的沉淀和心灵的触动。这日落之美是如此短暂,直让人心生无尽的遐想与哀愁。想想自己虽年事已高,须发皆白,却仍需日行万里,无论人行何处,孤独与忧愁始终相伴,一种漂泊无依之感油然而生,久久挥之不去。如今到绣湖故地重游,是该再享用一回那久负盛名的“鲈鱼鲙”了。春色初回万象新,在湖滨长满繁盛香草的小岛,又呈现出一派美好的景象。春雨潇潇时,正适合钓鱼,此时该去买一件蓑衣来,到湖畔静享悠闲垂钓之乐。任凭风吹浪打,请为我向着飞翔的沙鸥致意。
整首诗意境深远。诗人通过对绣湖景色和人事的交错描写,既勾勒出一幅夕阳西下时的凄凉与孤寂的画面,渲染出一抹忧伤的色彩,又写尽了初春时节的绣湖之景,让人心怀希望,抒发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喜悦之情,展现了诗人对自然和自由生活的向往。
一
陆游,字务观,号放翁,越州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他出身名门望族、江南藏书世家。高祖陆轸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进士,官至吏部郎中;祖父陆佃,官至尚书右丞;父亲陆宰通诗文,曾任京西路转运副使。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,成长在偏安的南宋,民族的矛盾、国家的不幸、家庭的流离,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他一生宦海浮沉,历经坎坷。初入仕途时,便因秦桧的刁难,举步维艰;后又因“结交谏官、鼓唱是非,力说用兵”的罪名被罢免了官职。
但陆游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,一生笔耕不辍,尤以诗的成就为最,在南宋诗坛占有重要地位。自言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,存世有九千三百余首。他的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:其前期诗颇能自出机杼,才气超然;中期诗因遭时势之逼迫,兼以意气豪迈,寄身戎马,大有横戈跃马、驱驰尘境之气概;晚年蛰居故乡山阴后,诗风趋向质朴而沉实,诗境看似平淡却意旨深湛,不时流露苍凉的人生感慨。陆游的这首《题绣川驿》,是其中年时期的作品,是他入闽赴任途中在绣川驿游绣湖时所作,时年54岁。
陆游与义乌颇为有缘。这从《题绣川驿》的首句“绣川池阁记曾游”就可以看出,他对绣湖并不陌生。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,年仅6岁的陆游随父亲陆宰从山阴避祸东阳安文(今磐安县城),投奔磐安义军领袖陈宗誉。陆游在磐安的三年间,闲暇之时曾随父亲游历磐安山水,结交了社会贤达,也到过东阳、义乌一带交游作客。
古代仕官异地赴任,途中常常要经历漫长又艰苦的渡江涉水、翻山越岭。陆游曾有两次赴闽任职的经历,途中路过东阳时,曾写下与之有关的诗篇,其间就有可能路过义乌歇脚。
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冬,已经34岁的陆游奉命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,这是他仕途的起点。上任途中,陆游从山阴经东阳、丽水、龙泉到福建浦城,再由浦城顺闽江而下前往宁德。几个月后,陆游由宁德主簿调任福州决曹。绍兴三十年(1160年)初春,陆游奉命从福建卸任至临安任职。陆游这一次从福州至临安走的是海道,至温州登陆,再经括苍、东阳北上。在从福州北归途经东阳时写下了两首诗:其一为《东阳观酴醾》,其二为《东阳道中》。
二十年后,陆游第二次入闽任职。宋淳熙五年(1178年)初,陆游从四川卸职,结束了蜀中生活,回到京城临安(今浙江杭州)。到临安不久,陆游应召拜见宋孝宗。朝廷任命陆游出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(管理平常税收、茶盐税收的主管),赴建安(今建瓯)任所。他在上任前先回家。这年十月,陆游从山阴出发,经诸暨、义乌、衢州、江山、仙霞岭等地,至这年十一月间进入福建浦城,冬抵建安任所。入闽上任途中到了义乌,陆游可谓旧地重游,数十年来四处奔波,早已须发苍苍,却仍壮志难酬,平添了几分愁绪。于是,他把一腔愁绪写入《题绣川驿》的诗句中。
二
从《题绣川驿》的首句“绣川池阁记曾游”还可以看出,宋时的绣湖之滨,亭台楼阁、轩榭廊舫遍布,为繁华之所。自宋代起,名门望族、文人雅士便争相在绣湖边修建别业,构筑了这些精美建筑。
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宋、元间,好事者构亭榭、植花木,为游赏之地,凡二十四处。岁久荒废。”“宋绍兴十二年(1142年),沈直方(县丞)建有慈和堂、简静堂、湖山第一台、净照关、晚照亭。旧在县西一百五十步。”“绍兴十三年(1143年),知县董爟请为放生池,禁采捕,率民治湖灌田如旧。”
《永乐大典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。在《永乐大典》(残卷)第96章中,即有关于绣川湖“秋光阁”的记载:“湖之傍又有月岩、秋光阁、登高台。大观三年(1109年),邑官祷雨,因筑堤以通往来,即柳洲造塔。”
驿站分水驿和陆驿,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以及来往官员途中食宿、换马的场所。封建君主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、指令发布与反馈。隋唐时期,其邮驿的建设也达到了空前的繁盛,绣川驿便初建于唐朝,且在古书中多有记载。
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中写道:“绣川驿,在县西北一百步。旧在县东四十步。唐名双栢驿,宋名义乌驿。熙宁五年(1072年),知县茹敦礼徙县西一百五十步。后枕绣湖因改名绣川驿。绍兴十五年(1145年),知县董爟重建。后有清旷亭。乾道四年(1168年),知县张谹更名德星堂。元至正十七年(1357年),佥绣川站徙至于今所,即旧尉廨(指县尉的官署)也。今废。”
另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绣川驿……熙宁五年(1072年),知县茹敦礼改为酒务,徙驿于县西一百五十步……元至正十七年(1357年),佥绣川站徙至县西北一百步旧尉司所。”“尉司,县北一百八十步。旧在县北五十步。宋绍兴间徙县西北一百步,县学故址也。元改绣川驿。”因此,作为往来官员中途暂歇的旅舍,陆游在前往福建赴任路过绣湖时,走进绣川驿歇脚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按三十里设置一驿站(如地势险阻,则按照实际地理形势设置),十里设置一急递铺,古时在义乌境内曾设有三个驿站,除了绣川驿,还有待贤驿、龙祈驿。待贤驿建于唐朝,龙祈驿则建于元朝,《崇祯义乌县志》对此有记:“待贤驿,去县北三十里。唐文德元年(888年)置,废久。”“龙祈驿,去县北五十五里。元至元二十五年(1288年),佥龙祈站创置。今废。”
三
绣川驿因其地理位置和历史事件而闻名,如同一个巨人神经元的重要节点,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,吸引了不少达官显贵来此歇脚。宋乾道四年(1168年)的春天,文惠公洪适在退休回乡途中曾在绣川驿停留。
在南宋,以爱国志士洪皓为首,与其三子洪适、洪遵、洪迈并称著名的“四洪”。其中,洪遵为状元,洪适为榜眼,洪迈也是有名的大文学家。洪皓是南宋著名忠臣,江西饶州(今鄱阳)人,宋高宗建炎三年(1129年)五月,以徽猷阁待制,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,羁留十五年后遇赦归宋,擢徽猷阁直学士,封为魏国公,卒赠太师,谥忠宣。洪皓的三个儿子,都曾位居(或相当)宰相之职:长子洪适,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,去世后谥号文惠;次子洪遵,曾任翰林学士承旨,迁同知枢密院事;三子洪迈,曾任翰林学士,加端明殿学士。
《夷坚志》便是由洪迈所创作的文言志怪集,是自《搜神记》以来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。作者以夷坚自谓,将其书比作《山海经》。从文学发展史上看,《夷坚志》是宋代志怪小说发展到顶峰的产物,是着重反映洪迈所经历时代社会生活、宗教文化、伦理道德、民情风俗的一面镜子,为后世提供了宋代社会丰富的历史资料,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陆游有诗《题夷坚志后》云:“笔近反离骚,书非支诺皋。岂惟堪补史,端足擅文豪。驰骋空凡马,从容立断鳌。陋儒那得议,汝辈亦徒劳。”
作者洪迈在《夷坚志》戊卷五中,就记载了其兄文惠公洪适与绣川驿的一段故事:“绣川驿:乾道四年(1168年)春,文惠公自会稽帅请祠归,将至婺州之义乌。知县事张谹,先期汛扫绣川驿。邑吏掌供办者宿其中。夜未艾,月色朦胧,闻外人往来行步甚武,疑为盗也。谨伺之,历神人十余辈,长者丈许,众惧,不敢出户,复就寝,竟夕不遑宁。明日而文惠至。盖故相所临,必有神物为之导卫耳。”
“会稽帅”,指文惠公洪适曾经做两浙东路的安抚使,类似现在的省长,有兵权。“祠归”,指的是“奉祠归”,宋代安排退休官员的一种方式,发给退休俸禄。“汛扫”,即洒扫。“未艾”,还没有到尽头。“遑宁”,释义为安逸、安宁。
洪迈在讲述“绣川驿”的故事时写道:宋乾道四年春天,文惠公洪适在会稽大帅的位置上向朝廷请求了祠禄,退休回老家,快走到婺州义乌县时,知县张谹预先派人打扫收拾了绣川驿。县里负责迎来送往、补充驿站生活供给的小吏们,也提前到驿站准备,当夜还住在驿站。没到夜深之时,屋外月色朦胧,小吏们忽然听到驿站外有人往来行走的脚步声,脚力雄劲。他们怀疑可能来了盗匪,于是很谨慎地向外偷窥,却看见经过十多个神人,有的身高过丈。小吏们都感到很害怕,不敢出门,于是继续睡觉,但整个晚上心里都不踏实。到了第二天,文惠公来了。估计夜里的奇事是因为做过右丞相的洪适要来,冥冥中会有一些神灵在做先导护卫的工作吧!
四
绣川驿在古诗词中曾多次被提及,占有一席之地。宋代诗人陈棣(约在1140年前后在世)曾赋有《题义乌县绣川驿》诗一首。其诗云:“湖漾晴波万叠秋,山攒远翠两眉愁。一川暝色烟欹柳,千里寒光月满洲。直恐断堤横北固,定知绝景冠东州。尘缨欲濯沧浪水,愧见沙头双白鸥。”
陈棣,字鄂父,青田人,曾以父荫出任广德军掾属,官至奉议郎、通判潭州。其父陈汝锡曾有诗为黄庭坚所赏识,陈棣则是宋季江湖诗派的先导者,在文学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记,后人评价其诗“大都平易近情,不失风旨”。在《题义乌县绣川驿》一诗中,诗人以简洁的语言、细腻的笔触,描绘了绣川驿四周的湖光山色,将绣湖的波光、山脉的苍翠、夜色中的烟雾和月光等融合在一起,勾勒出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。
此诗的大致意思是:见绣川湖的湖面波光粼粼,像是有无数层秋水交织在了一起。远山如黛,层峦叠嶂,看上去仿佛两道紧蹙的眉头,给人以忧郁感。那在暮色中静静流淌的河流,以及被烟雾笼罩的柳树,无不产生一种朦胧而恬静的美感。一轮明月在洲岛的上空升起,寒冷的月光一泻千里,天色与湖光上下呼应。我担心这河堤一旦决了口,湖水就会直冲至北固山前。我深知这美好无比的风景也是浙东所有州中最出色的。我准备用沧浪之水来洗净这尘俗之事,却愧见沙洲上那一对纯洁而自由的白鸥。
陈棣所写的这首诗以自然景色为背景,以其细腻的笔触和形象生动的描写,写尽了绣川驿的胜景,让人沉醉于绣川湖的湖光山色中,并透露出作为天涯漂泊客的那份孤寂与哀愁。无独有偶,陈棣还写过一首《再过绣川驿》,描写的是秋日绣川驿的场景,可见其对绣川驿感情之深。其诗云:“霜林病叶日凋残,更觉平芜眼界宽。天外碧云山共远,阶前明月水争寒。愔愔夜气侵肌骨,戢戢诗愁入肺肝。欲去自怜心未惬,为君满意更重看。”
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: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。” 陈棣重游绣川驿,因心境不同,所以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。这首诗的意思是:秋霜中的树林,枯叶已日渐凋零,那平坦的原野看起来更加开阔无边。天边的云彩与远山交融在了一起,台阶前的寒冷江水,映照出明月的惨淡光影,使夜色显得更加清冷。在这个静寂的夜晚,寒气逼人侵肌透骨,如麻的诗情已涌入心肺之中。想要离去,心中却自感不舍,为了满足你的意愿,我再次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。
喻良能,字叔奇,号香山,宋绍兴二十七年(1157年)进士,官至国子博士、工部郎中。他曾写过《题绣川驿揖秀亭次张明府韵》一诗。其诗曰:“一色苍波百顷烟,直楣横槛覆华椽。从来好景无今日,何限清诗似昔贤。把盏有山来酒面,凭栏无路到愁边。我来正值雨新足,芳草芊芊绿满川。”
此诗的大致意思是:诗人在登临绣川驿揖秀亭时远眺,但见一望无垠的苍茫水域碧波荡漾,烟波浩渺,水天一色。竖立的柱子和水平的横梁,纵横交错,宏伟壮观,安放在檩上的椽子则是层层叠叠、华丽精致,整个亭子显得分外富丽堂皇。历来良辰美景并非仅今日才有,而是历久弥新,纵观那些清雅而有意境的诗句,都展现了古代圣贤的智慧和才华。大家把酒言欢,酒面上映出远山的倒影;扶栏眺望时,却是愁绪万千、绵绵不绝,更无处诉说内心的凄凉与悲戚。诗人来到这里时,刚下过一场雨,雨水丰沛。在新雨的滋润下,绣川湖畔芳草葱茏,绿意盎然,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。
从喻良能所写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,宋时在绣川驿旁还建有揖秀亭。从字面上来看,“揖”是聚集的意思,“揖秀亭”可称得上是尽揽山川秀色之亭。在亭的周边建有廊桥渡水、假山花木等园林建筑,玲珑而小巧,古朴而雅致,为绣川驿增色不少。游人登临此亭,山川秀丽景色便可尽收眼底。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