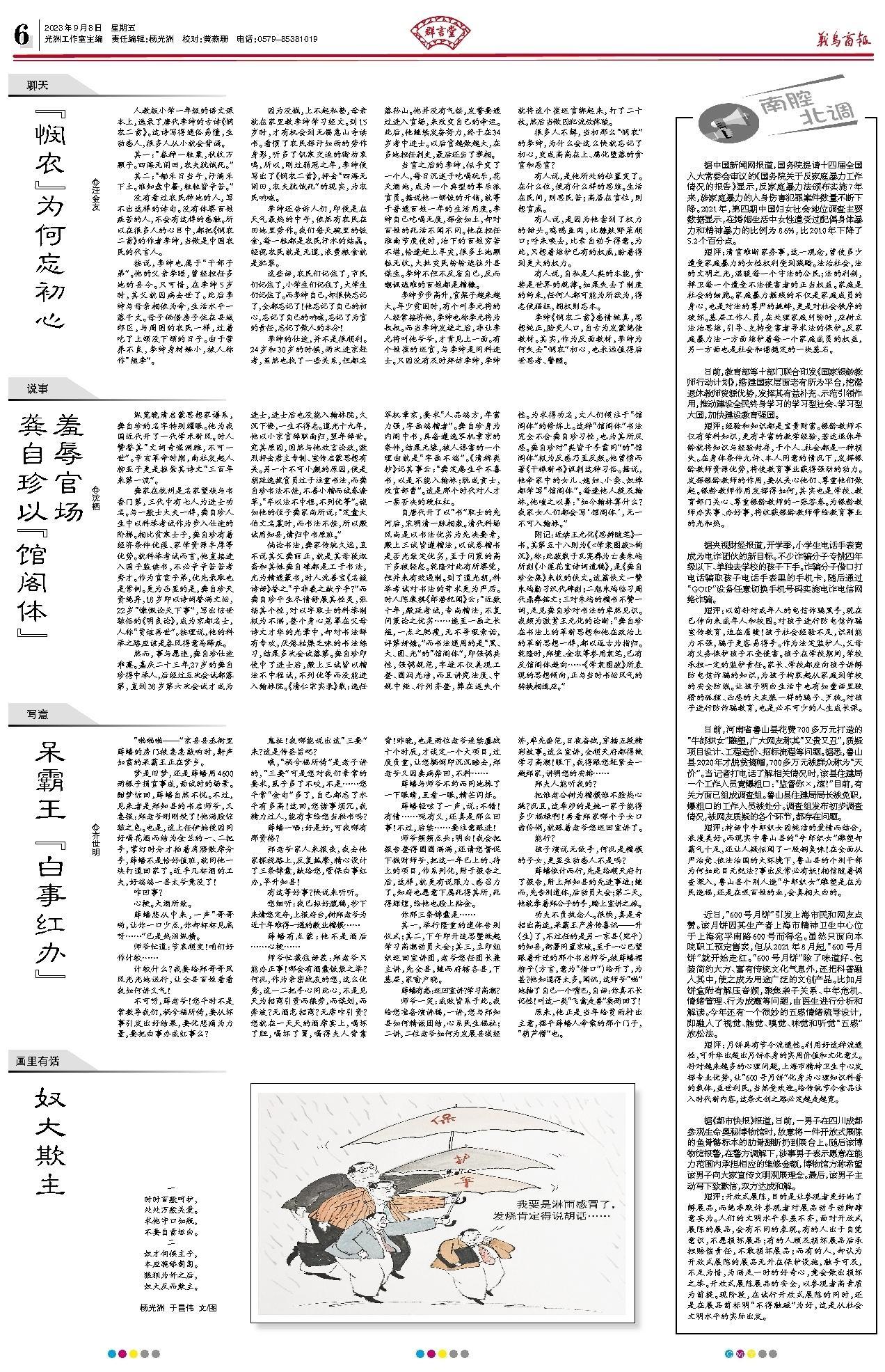纵览晚清启蒙思想家谱系,龚自珍的名字特别耀眼。他为我国近代开了一代学术新风。时人赞誉其“文词奇崛渊雅,不可一世”。辛亥革命时期,南社发起人柳亚子更是推崇其诗文“三百年来第一流”。
龚家在杭州是名家望族与书香门第,三代中有七人为进士功名。与一般士大夫一样,龚自珍人生中以科举考试作为步入仕途的阶梯。相比贫寒士子,龚自珍有着经济条件优渥、家学资源丰厚等优势。就科举考试而言,他直接进入国子监读书,不必辛辛苦苦考秀才。作为官宦子弟,优先录取也是常例。更为凸显的是,龚自珍天资绝异,18岁即以诗词誉满文坛,22岁“慷慨论天下事”,写出惊世骇俗的《明良论》,成为京都名士,人称“贾谊再世”。按理说,他的科举之路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
然而,事与愿违,龚自珍仕途乖蹇。嘉庆二十三年,27岁的龚自珍得中举人,后经过五次会试都落第,直到38岁第六次会试才成为进士,进士后也没能入翰林院,久沉下僚,一生不得志。道光十九年,他以小京官辞职南归,翌年辞世。究其原因,固然与他放言论政,激烈抨击君主专制、宣传启蒙思想有关。另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,便是朝廷选拔官员过于注重书法,而龚自珍书法不佳,不善小楷而试卷潦草,“卒以法不中程,不列优等”。诚如他的侄子龚家尚所说:“定盦大伯文名震时,而书法不佳,所以殿试用知县,请归中书原班。”
倘论书法,龚家传统久远,且不说其父龚丽正,就是其母段淑斋和其妹龚自璋都是工于书法,尤为精通篆书,时人沈善宝《名媛诗话》誉之“子非羲之献子乎?”而龚自珍平生尽情舒展其性灵,张扬其个性,对以字取士的科举制极为不满,整个身心笼罩在父母诗文才华的光晕中,却对书法鲜有专攻,厌倦枯燥乏味的书法练习,结果多次会试落第。龚自珍即使中了进士后,殿上三试皆以楷法不中程试,不列优等而没能进入翰林院。《清仁宗实录》载:选任军机章京,要求“人品端方,年富力强,字画端楷者”。龚自珍身为内阁中书,具备遴选军机章京的条件,结果无缘,被人谗害的一个理由就是“字画不端”。《清稗类抄》记其事云:“龚定庵生平不喜书,以是不能入翰林;既成贡士,改官部曹”。这是那个时代对人才一票否决的硬杠杠。
自唐代开了以“书”取士的先河后,宋明清一脉相袭。清代科场风尚是以书法优劣为先决要素,殿上三试皆遴楷法,以试卷楷书是否光致定优劣,至于问策的高下多被轻忽。乾隆对此有所察觉,但并未有效遏制。到了道光朝,科举考试对书法的苛求更为严厉。时人陈康褀《郎潜纪闻》云:“近数十年,殿廷考试,专尚楷法,不复问策论之优劣……遂至一画之长短,一点之肥瘦,无不寻瑕索诟,评第妍媸。”而书法通用的是“黑、大、圆、光”的“馆阁体”,即强调共性,强调规范,字迹不仅美观工整、圆润光洁,而且讲究法度、中规中矩、行列齐整,弊在迷失个性。为求得功名,文人们倾注于“馆阁体”的修炼上。这种“馆阁体”书法完全不合龚自珍习性,也为其所厌恶。龚自珍对“类皆千手雷同”的“馆阁体”极为反感乃至反叛。他曾愤而著《干禄新书》讽刺这种习俗。据说,他命家中的女儿、媳妇、小妾、奴婢都学写“馆阁体”。每逢他人提及翰林,他嗤之以鼻:“如今翰林算什么?我家女人们都会写‘馆阁体’,无一不可入翰林。”
附记:近读王元化《思辨随笔》一书,其第五十八则为《<学隶图跋>钩沉》,称:此跋载于孔宪彝为亡妻朱屿所刻《小莲花室诗词遗稿》,是《龚自珍全集》未收的佚文。这篇佚文一赞朱屿勤习汉代碑刻;二勉朱屿临习周代鼎彝铭文;三对朱屿的楷书不赞一词,足见龚自珍对书法的卓然见识。我颇为激赏王元化的论断:“龚自珍在书法上的革新思想和他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一样,都以返古为指归。乾隆时,郑燮、金农等参用隶笔,已有反馆阁体趋向……《学隶图跋》所表现的思想倾向,正与当时书坛风气的转换相适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