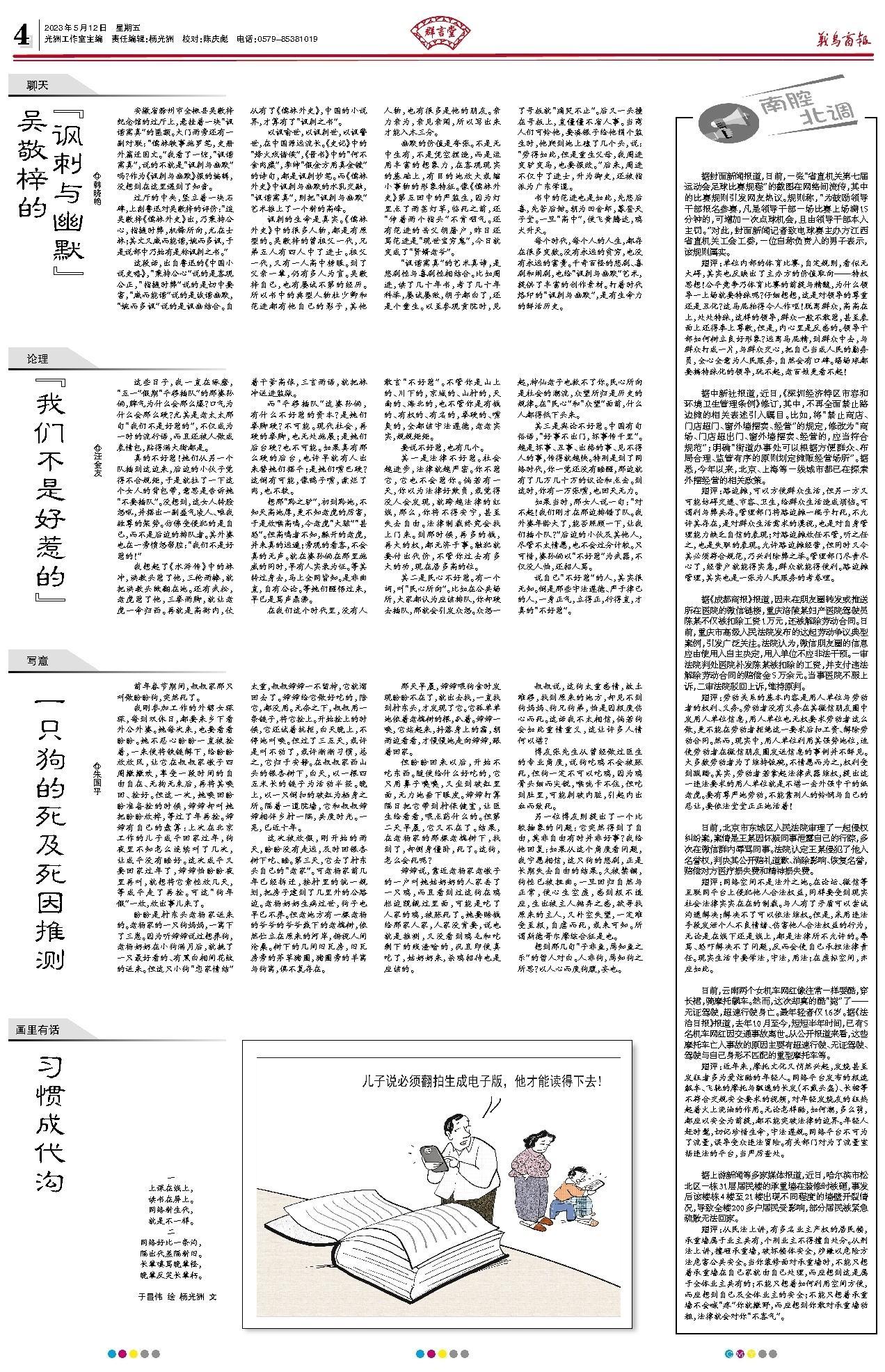前年春节期间,叔叔家那只叫做盼盼狗,突然死了。
我刚参加工作的外甥女琛琛,每到双休日,都要来乡下看外公外婆。她每次来,也要看看盼盼。她不忍心盼盼一直被拴着,一来便将铁链解下,给盼盼放放风,让它在叔叔家墩子四周撒撒欢,享受一段时间的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后,再将其唤回、拴好。但这一次,她唤回盼盼准备拴的时候,婶婶却叫她把盼盼放掉,等过了年再拴。婶婶有自己的盘算:上次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成平回家过年,狗夜里不知怎么连续叫了几次,让成平没有睡好。这次成平又要回家过年了,婶婶怕盼盼夜里再叫,就想将它索性放几天,等成平走了再拴。可这“狗年假”一放,放出事儿来了。
盼盼是村东头老杨家送来的。老杨家的一只狗妈妈,一窝下了三崽。因为听婶婶说过想养狗,老杨奶奶在小狗满月后,就挑了一只最好看的、有黑白相间花纹的送来。但这只小狗“恋家情结”太重,叔叔婶婶一不留神,它就溜回去了。婶婶给它做好吃的,陪它,都没用。无奈之下,叔叔用一条链子,将它拴上。开始拴上的时候,它还试着抗拒,白天晚上,不停地叫唤。但过了三五天,或许是叫不动了,或许渐渐习惯,总之,它归于安静。在叔叔家西山头的银杏树下,白天,以一根四五米长的链子为活动半径。晚上,以一只倒扣的破缸为栖身之所。隔着一道院墙,它和叔叔婶婶相伴乡村一隅,共度时光。一晃,已近十年。
这次被放假,刚开始的两天,盼盼没有走远,及时回银杏树下吃、睡。第三天,它去了村东头自己的“老家”。可老杨家前几年已经拆迁,按村里的统一规划,把房子建到了几里外的公路边。老杨奶奶生病过世,狗子也早已不养。但老地方有一棵老杨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老槐树,依然伫立在原来的河岸,俯视人间沧桑。树下的几间旧瓦房,旧瓦房旁的茅草猪圈,猪圈旁的羊窝与狗窝,俱不复存在。
那天早晨,婶婶喂狗食时发现盼盼不在了,就出去找,一直找到村东头,才发现了它。它孤单单地依着老槐树的根,趴着。婶婶一唤,它站起来,抖落身上的霜,朝两边看看,才慢慢地走向婶婶,跟着回家。
但盼盼回来以后,开始不吃东西。随便给什么好吃的,它只用鼻子嗅嗅,又坐到破缸里面,无力地垂下眼皮。婶婶打算隔日把它带到村保健室,让医生给看看,喂点药什么的。但第二天早晨,它又不在了。结果,在老杨家的那棵老槐树下,找到了,却侧身僵卧,死了。这狗,怎么会死呢?
婶婶说,靠近老杨家老墩子的一户叫她姑奶奶的人家丢了一只鸡,而且看到过这狗在鸡栏边觊觎过里面,可能是吃了人家的鸡,被胀死了。她要赔钱给那家人家,人家没肯要,说也就是推测,又没看到鸡毛和吃剩下的残渣啥的,况且即便真吃了,姑奶奶来,杀鸡招待也是应该的。
叔叔说,这狗太重感情,故土难移,找到原来的地方,却见不到狗妈妈、狗兄狗弟,怕是因极度伤心而死。这话我不太相信,倘若狗会如此重情重义,这让许多人情何以堪?
博友张先生从曾经做过医生的专业角度,说狗吃鸡不会被胀死,但狗一定不可以吃鸡,因为鸡骨头细而尖锐,喉咙卡不住,但吃到肚里,可能刺破内脏,引起内出血而致死。
另一位博友则提出了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:它突然得到了自由,莫非自由有时并非好事?我给他回复: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,我宁愿相信,这只狗的悲剧,正是长期失去自由的结果。久被禁锢,狗性已被扭曲。一旦回归自然与正常,便心生空虚,感到极不适应,生出被主人抛弃之感,欲寻找原来的主人,又扑空失望,一定难受至极,自虐而死,或未可知。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也。
想到那几句“子非鱼,焉知鱼之乐”的哲人对白。人非狗,焉知狗之所思?以人心而度狗腹,妄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