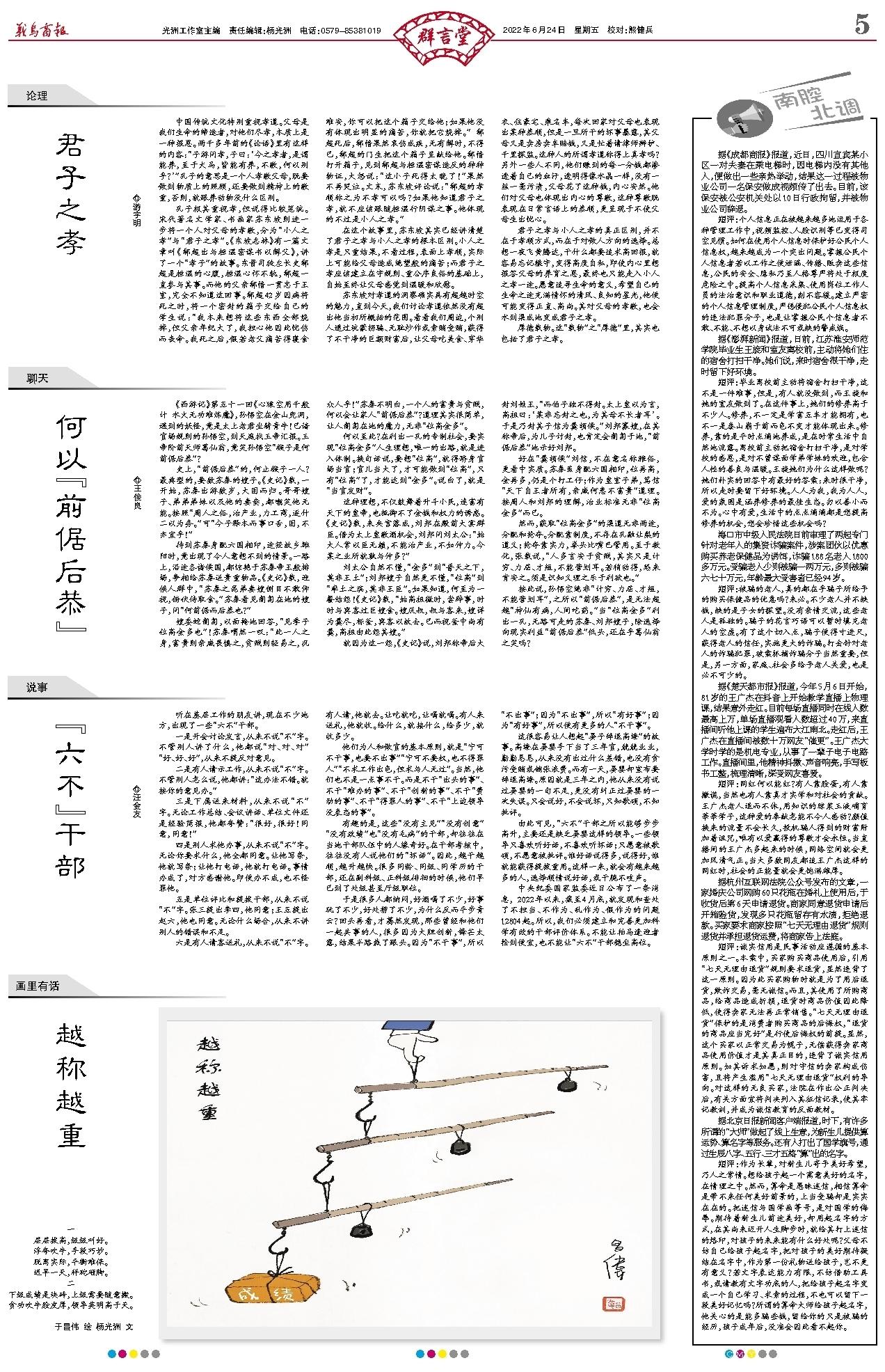《西游记》第五十一回《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》,孙悟空在金山兜洞,遇到的妖怪,竟是太上老君坐骑青牛!已谙官场规则的孙悟空,到天庭找玉帝汇报。玉帝阶前天师葛仙翁,竟笑孙悟空“猴子是何前倨后恭”?
史上,“前倨后恭”的,何止猴子一人?最典型的,要数苏秦的嫂子。《史记》载,一开始,苏秦出游数岁,大困而归。哥哥嫂子、弟弟弟妹以及他的妻妾,都嘲笑他无能。按照“周人之俗,治产业,力工商,逐什二以为务。”可“今子释本而事口舌,困,不亦宜乎!”
待到苏秦身配六国相印,途径故乡雒阳时,竟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景。一路上,沿途各诸侯国,都惊艳于苏秦帝王般排场,争相给苏秦送贵重物品。《史记》载,迎候人群中,“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,俯伏侍取食。”苏秦看见匍匐在地的嫂子,问“何前倨而后恭也?”
嫂委蛇匍匐,以面掩地回答,“见季子位高金多也”!苏秦喟然一叹:“此一人之身,富贵则亲戚畏惧之,贫贱则轻易之,况众人乎!”苏秦不明白,一个人的富贵与贫贱,何以会让家人“前倨后恭”?道理其实很简单,让人匍匐在地的魔力,无非“位高金多”。
何以至此?在利出一孔的专制社会,要实现“位高金多”人生理想,唯一的出路,就是进入体制。换句话说,要想“位高”,就得跻身官场当官;官儿当大了,才可能做到“位高”,只有“位高”了,才能达到“金多”。说白了,就是“当官发财”。
这种理想,不仅鼓舞着升斗小民,连富有天下的皇帝,也抵御不了金钱和权力的诱惑。《史记》载,未央宫落成,刘邦在殿前大宴群臣。借为太上皇敬酒机会,刘邦问刘太公: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,不能治产业,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?”
刘太公自然不懂,“金多”到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;刘邦嫂子自然更不懂,“位高”到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。如果知道,何至为一餐结怨!《史记》载,“始高祖微时,尝辟事,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。嫂厌叔,叔与客来,嫂详为羹尽,栎釜,宾客以故去。已而视釜中尚有羹,高祖由此怨其嫂。”
就因为这一怨,《史记》说,刘邦称帝后大封刘姓王,“而伯子独不得封。太上皇以为言,高祖曰:‘某非忘封之也,为其母不长者耳’。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。”刘邦寡嫂,在其称帝后,为儿子讨封,也肯定会匍匐于地,“前倨后恭”地示好刘邦。
好在“羹颉侯”刘信,不在意名称雅俗,更看中实质。苏秦虽身配六国相印,位再高,金再多,仍是个打工仔;作为皇室子弟,笃信“天下自王者所有,亲戚何患不富贵”道理。按周人和刘邦的理解,治业标准无非“位高金多”而已。
然而,获取“位高金多”的渠道无非两途,分配和抢夺。分配靠制度,不存在孔融让梨的道义;抢夺靠实力,拳头比嘴巴管用。至于教化,张载说,“人多言安于贫贱,其实只是计穷、力屈、才短,不能营划耳。若稍动得,恐来肯安之。须是识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。”
按此说,孙悟空绝非“计穷、力屈、才短,不能营划耳”,之所以“前倨后恭”,是无法超越“神仙有病,人间吃药。”当“位高金多”利出一孔,无路可走的苏秦、刘邦嫂子,除选择向现实利益“前倨后恭”低头,还在乎葛仙翁之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