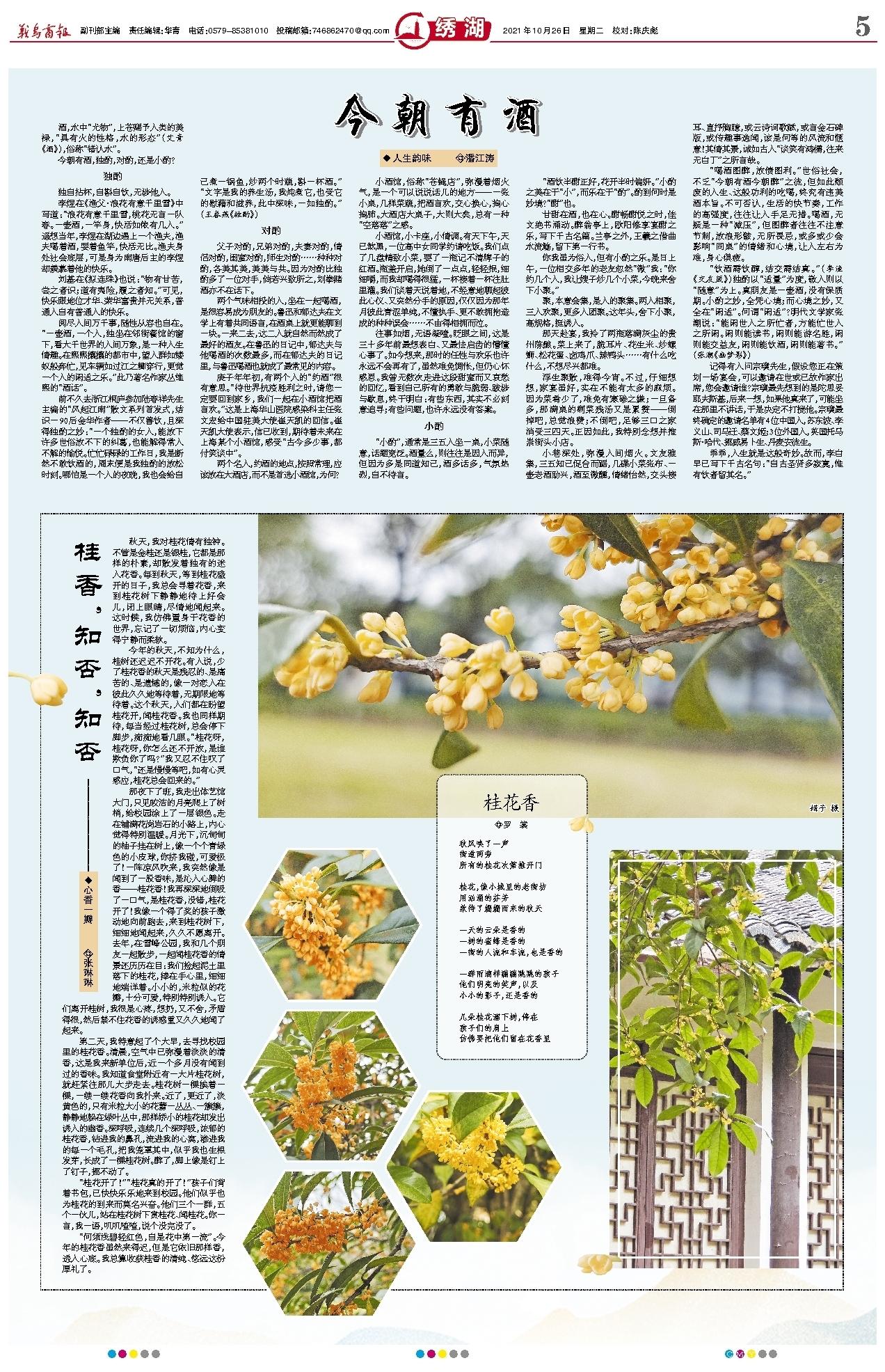酒,水中“尤物”,上苍赐予人类的美禄,“具有火的性格,水的形态”(艾青《酒》),俗称“错认水”。
今朝有酒,独酌,对酌,还是小酌?
独酌
独自拈杯,自斟自饮,无涉他人。
李煜在《渔父·浪花有意千里雪》中写道:“浪花有意千里雪,桃花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,一竿身,快活如侬有几人。”遥想当年,李煜在湖边遇上一个渔夫,渔夫喝着酒,耍着鱼竿,快活无比。渔夫身处社会底层,可是身为南唐后主的李煜却羡慕着他的快乐。
刘基在《拟连珠》也说:“物有甘苦,尝之者识;道有夷险,履之者知。”可见,快乐跟地位才华、荣华富贵并无关系,普通人自有普通人的快乐。
阅尽人间万千事,随性从容也自在。“一壶酒,一个人,独坐在邻街餐馆的窗下,看大千世界的人间万象,是一种人生情趣。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中,望人群如蝼蚁般奔忙,见车辆如过江之鲫穿行,更觉一个人的闲适之乐。”此乃著名作家丛维熙的“酒话”。
前不久去浙江桐庐参加陆春祥先生主编的“风起江南”散文系列首发式,结识一90后金华作者——不仅善饮,且深得独酌之妙:“一个独酌的女人,能放下许多世俗放不下的纠葛,也能解得常人不解的愉悦。忙忙碌碌的工作日,我是断然不敢饮酒的,周末便是我独酌的放松时刻。哪怕是一个人的夜晚,我也会给自己煮一锅鱼,炒两个时蔬,斟一杯酒。”“文字是我的养生汤,我炖煮它,也受它的慰藉和滋养,此中深味,一如独酌。”(王春燕《独酌》)
对酌
父子对酌,兄弟对酌,夫妻对酌,情侣对酌,闺蜜对酌,师生对酌……种种对酌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因为对酌比独酌多了一位对手,倘若兴致所之,划拳赌酒亦不在话下。
两个气味相投的人,坐在一起喝酒,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。鲁迅和郁达夫在文学上有着共同语言,在酒桌上就更能聊到一块。一来二去,这二人就自然而然成了最好的酒友。在鲁迅的日记中,郁达夫与他喝酒的次数最多,而在郁达夫的日记里,与鲁迅喝酒也就成了最常见的内容。
庚子年年初,有两个人的“约酒”很有意思。“待世界抗疫胜利之时,请您一定要回到家乡,我们一起在小酒馆把酒言欢。”这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回信。崔天凯大使表示,信已收到,期待着未来在上海某个小酒馆,感受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。
两个名人,约酒的地点,按照常理,应该放在大酒店,而不是首选小酒馆,为何?
小酒馆,俗称“苍蝇店”,弥漫着烟火气,是一个可以说说话儿的地方——一张小桌,几样菜蔬,把酒言欢,交心换心,掏心掏肺。大酒店大桌子,大则大矣,总有一种“空落落”之感。
小酒馆,小卡座,小情调。有天下午,天已煞黑,一位高中女同学约请吃饭。我们点了几盘精致小菜,要了一瓶记不清牌子的红酒。瓶盖开启,她倒了一点点,轻轻抿,细细嚼,而我却喝得很猛,一杯接着一杯往肚里灌。我们谈着天说着地,不经意地聊起彼此心仪、又突然分手的原因,仅仅因为那年月彼此青涩单纯,不懂执手、更不敢拥抱造成的种种误会……不由得相拥而泣。
往事如烟,无语凝噎。眨眼之间,这是三十多年前最想表白、又最怯启齿的懵懂心事了。如今想来,那时的任性与欢乐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,虽然难免惆怅,但仍心怀感恩。我曾无数次走进这段甜蜜而又哀愁的回忆,看到自己所有的勇敢与脆弱、跋涉与歇息,终于明白:有些东西,其实不必刻意追寻;有些问题,也许永远没有答案。
小酌
“小酌”,通常是三五人坐一桌,小菜随意,话题宽泛。酒量么,则往往是因人而异,但因为多是同道知己,酒多话多,气氛热烈,自不待言。
“酒饮半酣正好,花开半时偏妍。”小酌之美在于“小”,而乐在于“酌”。酌到何时是妙境?“酣”也。
甘甜在酒,也在心。酣畅酣悦之时,佳文绝书涌动。醉翁亭上,欧阳修享宴酣之乐,写下千古名篇。兰亭之外,王羲之借曲水流觞,留下第一行书。
你我虽为俗人,但有小酌之乐。是日上午,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忽然“微”我:“你约几个人,我让嫂子炒几个小菜,今晚来舍下小聚。”
聚,本意会集,是人的聚集。两人相聚,三人欢聚,更多人团聚。这年头,舍下小聚,高规格,挺诱人。
那天赴宴,我拎了两瓶落满灰尘的贵州陈酿。菜上来了,脆耳片、花生米、炒螺蛳、松花蛋、卤鸡爪、辣鸭头……有什么吃什么,不想尽兴都难。
浮生聚散,难得今宵。不过,仔细想想,家宴虽好,实在不能有太多的麻烦。因为菜肴少了,难免有寒碜之嫌;一旦备多,那满桌的剩菜残汤又是累赘——倒掉吧,总觉浪费;不倒吧,足够三口之家消受三四天。正因如此,我特别念想并推崇街头小店。
小巷深处,弥漫人间烟火。文友雅集,三五知己促台而踞,几碟小菜张布、一壶老酒助兴,酒至微醺,情绪怡然,交头接耳、直抒胸臆,或云诗词歌赋,或言金石碑版,或传趣事逸闻,该是何等的风流和惬意!其情其景,诚如古人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之所言哉。
“喝酒图醉,放债图利。”世俗社会,不乏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之徒,但如此颓废的人生、这般功利的吃喝,终究有违美酒本旨。不可否认,生活的快节奏,工作的高强度,往往让人手足无措。喝酒,无疑是一种“减压”,但图醉者往往不注意节制,放浪形骸,无所畏忌,或多或少会影响“同桌”的情绪和心境,让人左右为难,身心俱疲。
“饮酒需饮醇,结交需结真。”(李渔《交友箴》)独酌以“适量”为度,敬人则以“随意”为上。真朋友是一壶酒,没有保质期。小酌之妙,全凭心境;而心境之妙,又全在“闲适”。何谓“闲适”?明代文学家张潮说:“能闲世人之所忙者,方能忙世人之所闲。闲则能读书,闲则能游名胜,闲则能交益友,闲则能饮酒,闲则能著书。”(张潮《幽梦影》)
记得有人问宗璞先生,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,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,您会邀请谁?宗璞最先想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,后来一想,如果他真来了,可能坐在那里不讲话,于是决定不打搅他。宗璞最终确定的邀请名单有4位中国人,苏东坡、李义山、司马迁、蔡文姬;3位外国人,英国托马斯·哈代、挪威易卜生、丹麦安徒生。
乖乖,人生就是这般奇妙。故而,李白早已写下千古名句:“自古圣贤多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